梁思成:辽代的一块木头(第6/6页)
这年5月27日,梁思成写检讨反思:
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活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演讲,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4
1956年2月6日,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的梁思成,托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转呈一封信,表达了入党的愿望。信中说:“一个多月以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陪同您坐在宴会席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毛泽东见信甚感欣慰,明确表示支持梁的入党申请。这件事的最终实现,尽管还有两年多的考验过程,但却使梁思成逃过一劫。1957年的“引蛇出洞”,设计师陈占样在“一切以人民的名义”下,被打成右派。由于彭真的出面,梁思成没有成为右派。据说,毛泽东曾问彭真:“那个梁思成保住了没有?”彭真回答:“保住了,按照主席的指示办的。”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他还是梁任公的儿子嘛。”
免遭厄运的梁思成却从此选择了沉默。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十年!多么幸福的十年。”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
梁思成说过,“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也许梁思成没有料到,在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建筑师也同样不能独善其身。一次,梁思成听说河北宝坻县(2001年撤县设区,今属天津市)一座自己曾勘察过的辽代古庙被拆毁后,哀叹道:“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辛波丝卡,在其诗集《一百种乐趣》中,有一篇题为《写于旅馆》。诗中写到“文物古迹的热爱者”梁思成。1945年,梁曾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他在为国民党政府及盟军编制敌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时,特地建议盟军在战争中要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奈良。日本把梁思成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并塑铜像纪念。诗人在诗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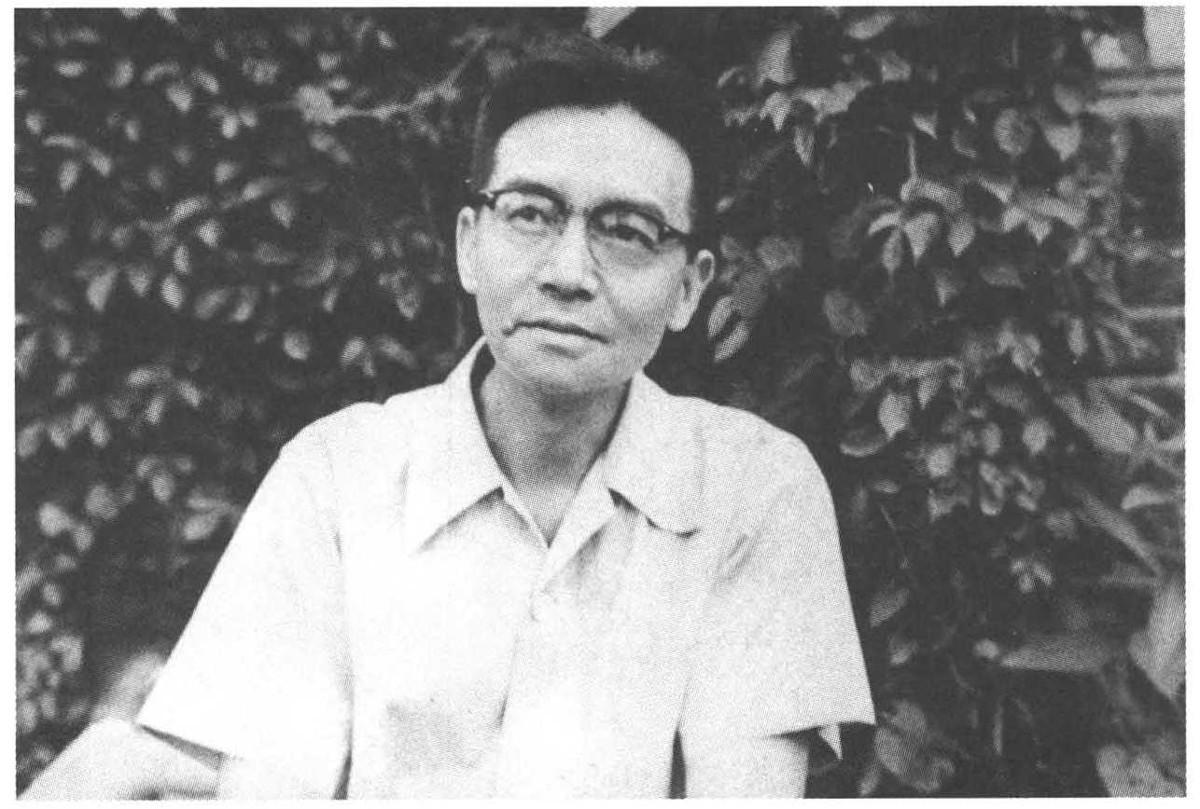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摄于清华大学胜因院。
京都是幸运的,
幸运而且遍布宫殿,
带飞檐的屋顶,
如音阶的楼梯。
古老而有情调,
坚硬而富活力,
它是木质的,
但从天上朝地上长,
京都是一座城,
动人的美令人落泪。
我是说真实的泪水,
出自一位先生,
一个行家,文物古迹的热爱者,
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在一张绿色桌子后,
大声地说:
等而次之的城市多的是呀!
然后在座位上,
突然开始啜泣。
就这样京都获救了……5
获救的还有梁思成——这块不朽的“辽代的木头”。
(本文照片由梁从诫、李光谟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