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第8/13页)
夏鼐领命考古所副所长时,梁思永表示:“所中一切事情都由我与郑先生管好了,我只希望你带一班小伙计们在外面多跑跑。”21履职仅一周,夏鼐就率队前往河南辉县。那次考古发掘,首次在安阳以外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代遗迹。次年春,他又风尘仆仆前往河南中、西部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证实了渑池县仰韶村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遗存,而且有龙山文化遗存,确认郑州二里冈是一处早于安阳殷墟的重要商代遗址。1951年10月,夏鼐马不停蹄,又赶到长沙。正当他俯下身子,潜心田野工作之时,又接到所里催促他返京的电文。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思想改造。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开始了第一场暴风骤雨。原中研院的旧人首当其冲,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
陶孟和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建院之初,根据分工,副院长陶孟和分管社会、历史、考古和语言四个研究所,兼任联络局局长。在他的建议下,他长期主持的原中研院社会所于1952年由南京迁北京。但不久社会学即被视为伪科学遭到批判,该学科后被取缔。后来,院领导调整分工,陶孟和分管编辑出版及图书馆工作。他在院长郭沫若的领导下,未必心情舒畅。时在中科院工作的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写道:
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22
原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回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孟和也是副院长,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史语所留下来的有语言学家丁声树、马学良、周祖谟,考古学家梁思永、夏鼐、郭宝钧、胡厚宣,历史学家杨志玖、逯钦立等。
针对“旧中国的考古发掘”,郭沫若写了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批判文章。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写道: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23
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在1952年8月2日的日记中,记下思想改造运动中群众对他提的意见:
(1)政治思想不够明确,在本所内缺乏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也缺乏主人态度,工作被动,与世无争,只做事务性工作;(2)本所在午门展览,夏所长直接领导布置,费了几万斤小米,但为什么要展览,为谁展览,都不够明确,能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应该详细检讨,从这上面即可以看到政治水平及服务的方向;(3)技术观点很重,对考古学的人没有团结,对后进的人也不重视培植训练(最近的考古训练班,听说夏所长又要请假回家);(4)做着所长,常觉得自己是研究员兼所长,无论在院领导的面前,郑、梁二所长的面前,以及群众面前,都是束手束脚,不知思想有什么顾虑,应该好好检讨。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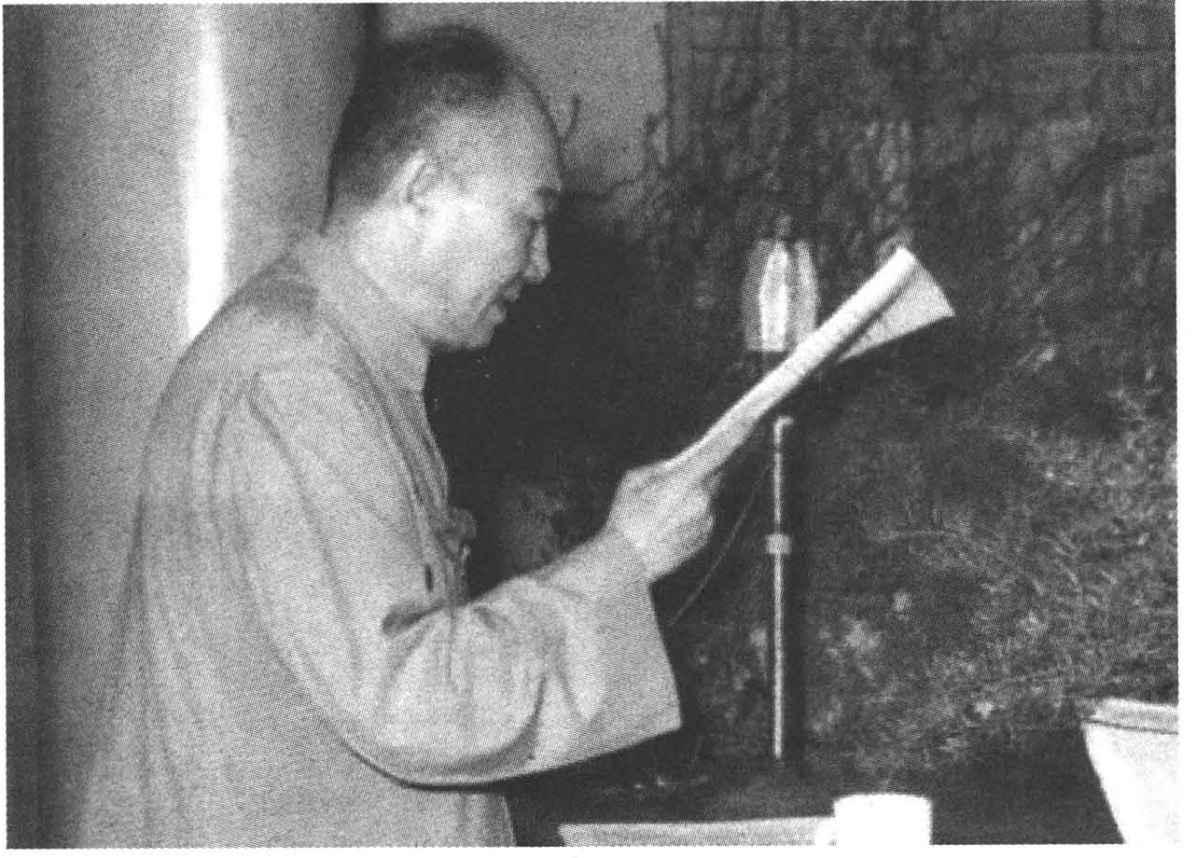
陶孟和在中科院大会上发言。
这些意见,应该说是“温水洗澡”。但他最大的烦恼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使其难以返回田野进行考古发掘。他在1952年12月31日的“总结”中说,本年“我只写了四篇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