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1:对作战的限制(第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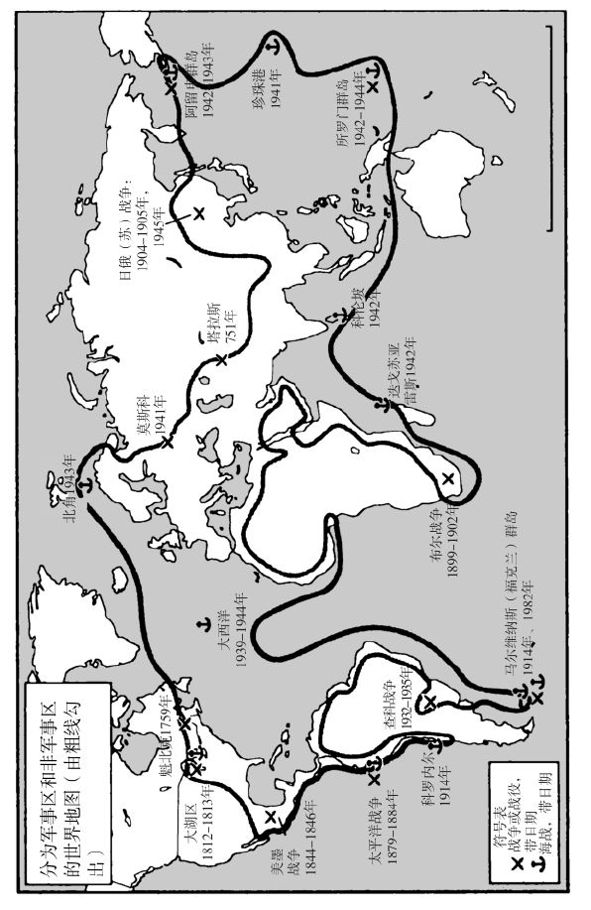
最引人注意的例子是土耳其欧洲部分的阿德里安堡,现名埃迪尔内。那里共发生过有记录的15次战斗或封锁,第一次发生在323年,最后一次在1913年7月。a
埃迪尔内从来不是,现在仍然不是大城市;人口一直没有超过10万。它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经常的兵家所争之地,不是因为它的财富或规模,而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三条大河的交汇处,这些大河的河谷提供了四通八达的通道——向西到马其顿的山区,向西北接保加利亚,向北则直达黑海岸边,而且它们流经欧洲最东南角的唯一开阔的平原,最后注入海洋。平原的另一边屹立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这座宏伟的城市,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大帝亲自选址定都,因为它位于欧亚两大陆分野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最是易守难攻。因此,从战略角度来看,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是姐妹城市,共同监视着黑海和地中海之间,以及南欧和小亚细亚之间的动静。因为君士坦丁堡无法从海上攻破,自从5世纪初修建了狄奥多西城墙之后更是固若金汤,于是,所有自小亚细亚来侵略南欧的入侵者都不得不在君士坦丁堡后侧的平原登陆;从黑海以北而来的入侵者由于陆地上喀尔巴阡山脉的阻拦,只能沿黑海西岸行进,结果也来到阿德里安堡的平原;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遭十字军洗劫之前是古罗马衰落以后西方世界最富庶的地方,对它一直垂涎三尺的欧洲入侵者在前来的路上也必须经过同一个平原。简而言之,阿德里安堡是地理学家所谓的亚欧陆桥的欧洲一端,亚洲有两条主要通道沿此陆桥进入欧洲,每当有大军沿任何一条通道自东向西或自西向东行进,阿德里安堡即不可避免地成为必争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城市从未能够发展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很少有别的地方像阿德里安堡那样如此明白地显示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战事的影响,然而,自古以来,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大部分军事活动密集的地区都或多或少地有迹可循。宽阔的河流、巍峨的山岳、茂密的森林形成了“天然边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边界也逐渐与之吻合;两者之间的空当为大军行进提供了通道。然而,过了这样的空当之后,哪怕没有明显可见的障碍,军队也很少能随心所欲地行动。即使没有堡垒要塞,只要修建有道路和桥梁,地理就成了一种微妙的重要因素,气候和季节则可以进一步加大它的作用。所以,在德国1940年对法国发动的突袭中,看起来好像打先锋的坦克冲破了阿登森林和默兹河的屏障后,就任意地横冲直撞,但实际上,它们的前进路线紧沿43号国家公路,而这条公路大部分又是沿公元前1世纪恺撒征服高卢后不久由古罗马人修建的道路铺设的。古罗马人和后人建造公路时都顺应地形依势修建,因此可以推断,德军的坦克指挥官无论怎样自以为能够到处畅行无阻,实际上都在遵守着法国北部10000年前冰川消退后留下的地表形状的古老规定。
研究一下德军闪电进攻法国一年后对苏联的入侵,同样可以看到自然法则的决定性作用。苏联西部似乎可以让侵略军,特别是机械化的侵略军任意驰骋。从苏联1941年的边界到600英里之外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一路上一马平川,没有一处高于500英尺的高地,而且这片几乎没有森林的广袤平原上的河流基本上都是东西流向,与侵略军的前进路线相平行,没有拦路的河流。应该没有,也的确没有任何固体的障碍阻拦侵略大军的前进。然而,在苏联中部,奔流着从苏联注入黑海和波罗的海的两条最大的河流——第聂伯河和尼曼河;它们的源头有许多支流,共同形成了普里佩特沼泽地,方圆40000平方英里,对军事行动是一大障碍,德军的参谋人员甚至把军情地图上标志着它位置的地方称为“国防军之空洞”(Wehrmacht hole),意思是那里没有任何得力的德军部队。结果,它成了苏联游击队袭扰德军后方的主要根据地。虽然游击队的行动不见得多么有效,但随着德军前线日益向东推进,苏联游击队使德军始终感到如芒在背。